一起听方舱医院里的故事!

年二十九退了机票,第一时间“请战”
早在1月24日除夕夜,首批广东省援鄂医疗队出发的当天晚上,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就发出了征集医护人员到一线去的倡议,邓晓龙、肖强和刘颖三位医生,都是在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他们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邓晓龙:
我觉得一个人从小到大,可能都有过一个保家卫国的英雄情结,我也有。当年在非典的时候,我主要是负责外围,在发热门诊,没有到非典的一线,所以我特别希望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报效国家。我们没有机会像解放军战士一样去保家卫国,但当这个国家遭遇瘟疫的时候,当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影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医生就要像战士一样冲上去。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想去帮助病人获得健康,捍卫他们健康的这种权利。
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救死扶伤是我们一个本职,我们常说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切都是以病人的生命安全、患者安全至上。当时准备回家,因为我爱人还在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听到有疫情之后,医院也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在大年廿九把机票退了,因为当时感觉可能会有要去抗疫的任务,我也在做这样的准备,也给家里人说了。但是后来去武汉的时候,是没有跟父母说的,害怕他们担心,只是跟爱人说了我要去。因为我的爱人曾经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她也非常理解,她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肖强:
我是一名医生,不管是脱产做研究也好,还是做什么,我都是一名医生,所以当国家面临重大瘟疫的时候,医生就应该站出来。我做课题研究,这并不影响我去前线做这些所谓的救治工作,因为我的看家本领还在。说到去到前线,我觉得对我做研究的思路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看到这些病人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去了以后,我发现我对科研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做科研,不仅是为了做了一些细胞,做一些动物,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把目标锁定在能够应用到临床,造福病人。
我去年和前年一直在研究肺部感染,只是我研究的肺部感染不是传染性的那种传染病,是常见的肺炎。我们知道肺炎是很常见的一个疾病,只是我们现在医疗水平提高,很多肺炎都能够治愈。在之前我已经有很多一手资料,关于肺炎治疗方面的。但这次肺炎不太一样,这次肺炎发病很急、很快、传染性很强。我们去到那边之后,看到这些病人,我就有一点新的想法,以后做研究的话,可能不但要做一些普通肺炎,更加要考虑到很有可能会有潜在一些重大肺炎的可能。
我爱人也是单位的一名医生,她还是很支持的,我作为一名呼吸内科相对专科的医生,对于这个新冠肺炎来说,我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我作为我们科室脱产去做研究的,相对来说没有在一线忙的,我更应该去,把自己的老本行发挥到前线去。
刘颖:
我是湖北恩施人,有5年的大学时光是在武汉度过的,所以说武汉是我的第二家乡也不为过。我相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家国情怀,我也不例外。除夕夜,我们都在值班,当时除了铺天盖地的很多报道之外,关于新冠肺炎,在我的大学同学群里面,我看到我的很多同学奋战在湖北的各个大小城市,他们很多人日夜奋战,大家都在那种无助的心境下就度过了那样一个除夕。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同学在群里面说,“大家发一点高兴的消息吧,一线人员心太苦了。”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我觉得他们太难了,其实我应该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相对他们来说,我已经过得特别好了,我真的很希望在那一刻能够飞回去帮助他们。
我做决定是很快的,我一旦决定的事,也会马上去做,当时写请战书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事情,虽然心里是这么想,就是决定后就写了。但当时没有跟家里人说,是因为家里人特别害怕,等到我们到了那边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当时我们第二批援鄂医疗人员也过去了,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看到我妈妈当时在我的朋友圈留了言,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内容,她又把它删除了,我知道她一定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我当时就告诉她,我已经到了武汉了。然后我妈妈就说,“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去一线,就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她甚至说,如果你们那边需要有人做饭的话,我可以去。
方舱医院里的故事
当普通市民宅在家里的时候,通过电视或者网络了解最新的疫情信息的时候,我们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却在抗“疫”的最前线,不分昼夜,与时间赛跑,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湖北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的病房里,发生了哪些故事?
邓晓龙:
我们所在的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是武汉最大的方舱,拥有1600张床位,我们是2月9日抵达武汉的,当时是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佛山医疗队主要是在方舱的西舱,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舱时候的情况,病人很多,有428个病人,我们的值班医生是5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5名大夫要面对400多个病人,即使都是轻症,他们有很多人不舒服,有很多问题要去处理,甚至有些病人因为隔离的时候很久,他的情绪很焦躁,有些病人在新冠肺炎中失去了亲人,或者是与亲人在不同的方舱隔离。他们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些人是崩溃的。所以我们不仅是治疗他的疾病,更多是要交流,稳定他们的情绪,消除他们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
我们的日常工作除了治疗轻症之外,还需要在轻症的患者中发现重症,有些病人的病情是有进展的,一旦发生重症的话,我们就要把他转出去,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救治。
我最深刻的是关于病人的,我们三位队友都经历了这2个病人,就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年近九旬的老人家,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六、七岁。这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进舱的时候,她是明确诊断为新冠,但是她的岁数太大了,生活不能治理,当时她的儿媳妇已经六十多岁,也是一位老人,跟她密切接触,也进了方舱来照顾她。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病人躺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时候,我们就深深感到了我们的责任感,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救治他们,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与家人团聚。
那个孩子也一样,这么小的孩子进到方舱,他可能对病情并不理解,他不停地跟他妈妈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我们当时确实很纠心,希望在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和孩子最好的救治方案,让他们早一点出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肖强:
去的时候,我是一名呼吸科医生,这次的新冠肺炎病人主要是呼吸道症状为主。去到方舱里面,面对这些病人有咳嗽、有气促或胸闷,这个在我平时日常工作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病的症状,但在方舱里面的病人与平时管的病人不太一样。因为平时管的病人大部分是既往的基础病也好,包括疾病的原因也好,包括它的发展趋势也好,我们都了如指掌,可以说胸有成竹。而这次新冠肺炎因为前面有太多的未知,这些病人我们只能按照国家的指导文件,还有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名呼吸科医生,面对病房里的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我就会根据这些去分析一些可能的原因,让他得到一些救治。比如有些人气促胸闷,他不一定是病情加重的,他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些药物可能会有影响。作为一个专科医生,可能在这方面相对来说经验是多一点。
至于科研这一块,去的时候我没有太想,因为当时就一个目标:想用自己的知识,尽快地帮病人解除痛苦,让他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刘颖:
方舱医院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它只是在国家危急的状态下的一个过度的产物,它并不是像我们印象中的医院,它就是一个大的仓库改建而成的。在那个地方,医疗设施是非常简陋的。大家会说,你们那里是收治轻症的病人,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在这么多的轻症患者中,我们必须要识别这里的危重症患者,我们要及时联系转院,不能耽误患者的治疗。
方舱医院里的患者,很多人的文化程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高,有的时候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些科普教育,而且他们的心情特别焦虑,所以我们做的是要去安抚他们的心。我觉得他们当时的焦虑除了来自于自己的身心受伤、家里人的离开,也有一个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他们对疾病的了解不够。当时在我们的队友支持下,我差不多每次进舱都会花上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跟他们做一些科普。科普的内容最主要的还是围绕新冠肺炎,比如怎样去预防它?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日常生活应该要注意什么?或者是出舱之后,回到家里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还有就是建立了我们的工作微信群,这是比较新的一个工作方式,因为当时我管理的病人是以中年女性患者为主,她们对我们的依从性也不是太高,而且一开始会很害怕自己的传染性疾病被其他人知道,所以她们是有抵触情绪的。刚开始在群里面号召大家把一些生命体征发给我的时候,大家是拒绝的。我觉得以真心换真心,当你非常认真投入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他人是能感受到的,从一开始她们的抵触,到后来就特别的信任。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警察,是里面的病人,他发微信告诉我,他说,“刘医生,知道你要上班了,这里的爹爹婆婆都把所有的检查资料、这段时间的检查结果都已经整理好了,就等着你上班要拿给你看。”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虽然我是湖北人,但我的武汉话讲得不是特别的好,就跟我的白话是一样的,会有一些外来口音,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听到一个家乡人的声音,对他们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会强迫自己用不是很熟练的武汉话跟他们交流,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交流效果特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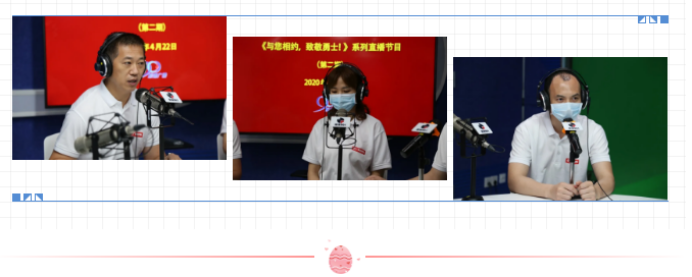
收获满满,再踏征途
目前,邓晓龙、肖强、刘颖三位医生已经返回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自己的岗位上,开始新的征途。在武汉的这段抗“疫”经历,也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邓晓龙:
我想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应急状况的处理,特别是在方舱,在很多病人、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如何去工作,在自己的工作经验上和工作管理上都一定的收获经验;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团队精神,我们从进舱到在舱内遇到很多突发情况,大家都能冲上去互相补位应付各种状况,很顺利地完成了我们的工作任务。
我们的方舱也实现五个零:就是患者零死亡,患者零投诉,医护人员的零感染等等。现在我们都已经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我所在的内分泌代谢科,刚刚成立了糖尿病足的专业亚组,就是我负责的,我也希望用自己所学的专长,能解决顺德地区糖尿病糖足等各方面慢性疾病的问题,发挥自己的一分光一分热。
肖强:
在武汉的经历肯定是此生难以磨灭的一个记忆,是一笔很宝贵的精神财富,肯定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至于研究,因为我个人一向以来对研究的态度就是,研究是为了应用到临床上来。接下来,还有近一年的研究时间,我也会以这个为导向,以病人的需求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去探索一些新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尤其是现在去过武汉之后,我更是感觉到要想更多的东西,比如应急的东西,我们遇到一些可疑的病人、可疑的样本时该怎么处理?这些是以前可能考虑得不够的地方,但现在和以后,就会想得很周到才行。
在武汉期间,当时全国在号召开发新冠肺炎的快速诊断和治疗的新产品。我也有与北京一个公司保持联系,他们经常与我交流,怎样去找突破点。在跟我交流之后,他们公司上个月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快速诊断病人核酸的产品,现在已经在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投入使用了。他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临床医生给予了很好的临床导向和启发,尤其是我在武汉的经历,包括见到病人的一些症状,我在当地的所见所闻等等。这些产品在南方医院顺德医院呼吸内科已经能做到一份样本来了之后,2小时内即能诊断出病人的核酸结果,不仅是咽拭纸,血液里面都能测出来这是不是新冠肺炎,这一块是很创新的一个产品。
刘颖:
我觉得武汉这一个多月的生活,是我印象中非常美好的一段岁月,我觉得它是一个年轻人在正确的年龄做的一个正确的事情,还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在那个地方,你经历了从绝望到开始有希望,然后到最后的春暖花开,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对自己也是一个升华,就好像是做了一个梦,现在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应该是梦醒了,不过我希望能够带着这种梦里面的美好,然后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

市民&网友:致敬!


市民罗生: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我们的抗疫英雄。这次的疫情,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感觉我们的中国非常强大,我们的人民非常团结,还有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非常敬佩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奔赴武汉,为了中国人民的安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也向他们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在武汉付出了每一份爱,我很感动。顺德的医护人员是很了不起了的,全国的医护人员也很了不起。


三位勇士节目后在直播室与节目组负责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