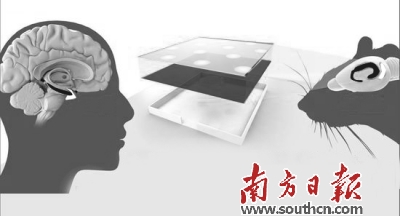
示意来自海马(黑色)的位置细胞与边界细胞与来自内嗅皮质(白色)的网格细胞共同构建了动物大脑中的“认知地图”。
天生不分东西南北,出门全靠一张嘴,大“路盲”、小“路痴”,今天坐反了地铁,明天走窜了胡同……
如果你是一个“路盲”,你是否经常羡慕那些认路高手——他们就像内置了一个活体GPS和一张高分辨率地图,怎样都不会迷失方向。怎么会这样?
10月6日揭晓的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恰恰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不认路,或许是天生的。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拥有美国和英国双重国籍的科学家约翰·奥基夫以及挪威科学家梅-布里特·莫泽和爱德华·莫泽夫妇,以表彰他们在大脑中发现了一种可以定位和导航的神经细胞——大脑“GPS”。
专家评价,三位获奖科学家的发现是大脑科学领域重大的基础性突破,使人类大脑如何运行定位系统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图景,该发现还有望打开治疗阿兹海默综合症的突破口。
位置、网格细胞合作定位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介绍: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身处何方?我们怎么找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径?我们如何存储这些信息,从而能够在下一次立即找到这条路?三位获奖科学家的研究解决了困扰科学界几个世纪的难题,揭示了大脑如何创建周围空间的“地图”,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定位路径。对大脑定位系统的认知,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大脑空间记忆的中枢机制。
实际上,早在1971年,奥基夫就在老鼠的一个叫“海马”的脑区里发现了大脑定位系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位置细胞”。经过反复研究,他发现,老鼠在房间的某个特定位置时,其大脑海马区的一些神经细胞总是处于激活状态,而老鼠移动到房间其他位置时,其他神经细胞则被激活。他因此得出结论:正是这些“位置细胞”,在大脑中形成了关于房间各点具体特征的“地图”。
然而仅仅拥有地图还不足以为我们导航,因为地图描述了每一个地方的特征,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地点的相对位置。我们还需要一个“经纬网”,让地图上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坐标。
2005年,莫泽夫妇关于“网格细胞”的研究正好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个叫做内嗅皮质的脑区里发现了大脑内置“GPS”的另一关键构成——“网格细胞”。这种细胞能形成坐标系,可以精确定位和寻找路径。此外,他们还研究出这些“网格细胞”是如何确定位置并导航的。
“感知位置和导航能力是最基本的大脑功能,对位置的感知能够令人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与周围物体的关系。”南方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朱心红教授介绍说,人类正是依靠这些空间能力才能在环境中识别、记忆并辨别方向。
“路盲”或因细胞“不好使”
如此说来,“路盲”“路痴”是否与大脑中的这些细胞“不好使”有关?
“‘路盲’或‘路痴’可能与位置和网格细胞有关,无论是网格细胞不好使,还是位置细胞功能太差,都有可能让你成为一个‘路盲’。”不过,朱心红同时强调,这一说法目前仍只是猜想,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实验数据支撑。
那“路盲”还有救吗?
在对位置细胞超过30多年的研究中,奥基夫的团队对这类细胞作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他们发现,和别的记忆一样,这种空间位置记忆既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遗忘,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加强,乃至终身保留。
比如,有研究就显示:出租车司机的海马区体积比其他人大。出租车司机每日每夜穿梭于成千上万条纵横交错的街道,随便给一个地址,他们能马上计算出最短的行进路线,开往准确的方向。这些长期训练,使得他们海马区的位置细胞比普通人强得多。
研究还表明,位置细胞具有可塑性:当环境发生一定变化时,这些记忆也可以根据环境改变作出修正,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在周遭环境不断变化时依然可以准确地记住一些地点。
此外,奥基夫还注意到位置细胞可分出一些亚类,比如有一类专门对活动边界——一堵墙或是一道无法跨越的沟壑敏感的神经细胞,并将其命名为“边界细胞”。有这些细胞存在,我们就不会“撞墙”了。
“发现大脑‘GPS’对于神经环路网络研究,尤其是对神经精神疾病,比如阿兹海默综合症等的神经环路异常研究更为有益。”朱心红表示。
阿兹海默症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
奥基夫在老鼠阿兹海默症模式下,证明了空间位置的能力弱化与动物空间记忆恶化有关。在该病初期,大脑定位细胞部分会频遭破坏,导致患者出现不认识路的症状。
在许多专家看来,空间记忆的神经细胞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该发现有助于了解病情初期造成空间记忆丧失的基本原理,是通往解决之道的一个重要飞跃。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找到有效方法来预防和治疗大多数的脑部疾病,而这一对脑部细胞的基础性研究可为此探路。”朱心红说。
新闻链接: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4-10/11/content_7357432.htm